周末一位兄弟要来上海,其实是路过,也就顺便看看我。
男人都是负心的东西,平常泡在虚拟的、现实的异性堆里,只在生意或者喝酒的时候想到了原来还有同性可以做好友。
上次见面是在另一个负心汉与异性的婚宴上,楼上“陪房”的一桌(不知道传统叫法是什么)青一色的“童男”:结婚的以及未婚有嗣的都不能上桌。只因男人的处子之身无从考证,这才勉强给新郎找了个借口放松了“童男”的要求,连同他自己小到七八岁的表侄们一起凑到八九个人。也亏得还有这些守节的老男人们没有成家,比如我、将要来上海的这小子以及其他杂碎,不然新郎肯定圆不了这个场。也就只有在全是非异性的场合,这些非异性的真实面目开始显露。
别看桌上这几人貌似人模人样,上谈天理人伦,下讲兄弟道义,但在喝酒的时候肯定装怂,一改往日在女生面前的豪气大度,都是举杯轻添,出奇的羞涩内敛;楼下的宴席早开过几席并逐个飨闭,楼上的这几位还谈笑自若,偶有倒地说些胡话的,要么是因酒量太小,要么是因准妻子来访,这才装个深沉悲情,非女人左扶右抱不能自已。
女人喜欢叫“臭男人”,是因为对手好装傻舞弊;男人推崇“纯爷们”,是因为实在物以稀为贵。
也就醉酒的时候才能使平常强颜欢笑的他吐些真言,因此,能找到几位发小一起醉倒、大肆追忆或面对痛楚何尝不是幸事。只是大家都有家了,或者即将有家了,这种放荡不羁的笑只能是越来越少。何况,酒文化已然被腐败势力侵蚀、宁人厌恶,真诚的桌上谈心变得越来越难。
周末一位兄弟要去巴黎,其实是路过,转机后就去非洲。
男人有时迫不得已,平常打情骂俏、甚至卖弄风骚,但在责任、压力面前毅然挺起了脊梁。
下次见面可能是在年后,并且今后除了春节,再也没有机会见个面、挥挥手。即便是他的准新娘,一如我们这些昔日的老友,再不能时时相伴左右。如果你有过异地相恋,那么你就能深刻体会这离别的滋味,以及作出离别抉择的酸涩。是的,有时为了多挣些银两,有时为了多些人生历练,有时甚至为家人所迫,抛弃七情六欲,只身于或孤独或混乱的角落,然后开始他自由而疯狂、五彩斑斓的夜生活。莫说苦,仰望高高在上的房价,能让农民子弟买上几平米已是幸福的憧憬;莫说甜,千里婵娟夜独眠。
八零后的生活就是这样,童年即便受尽老师的虐待毒打,如今想来,仍是那般的金色、纯情;青年即便泡尽周围的芙妹、蓉妹,面前的不过是一条为人奴隶的包身工之路。童年美好,是因为有那么多好伙伴陪着我们一起玩耍、被罚;青年痛苦,是因为再多的阳光雨露,也改变不了我们深处沙漠绝境的现实(The truth hurts)。
有时因为妈妈的一句呼唤,无论多大的风沙都愿意独闯;有时因为摇篮上那个懵懂的小脸,再强的烈日,都不愿停下。
谁都有疲倦悲伤的时候,男人也是如此。谁不想有个温馨甜美的小家,只是无奈的垄断、只是孤独的本性,使得我们或抗争、或逃离,或永远地埋在金字塔底。我知道地球的那一头是海,只是我们的根扎在了这火热土地;无论我们现在漂在哪里,我们最终还是要和心爱的人,长眠于那妈妈长眠的地方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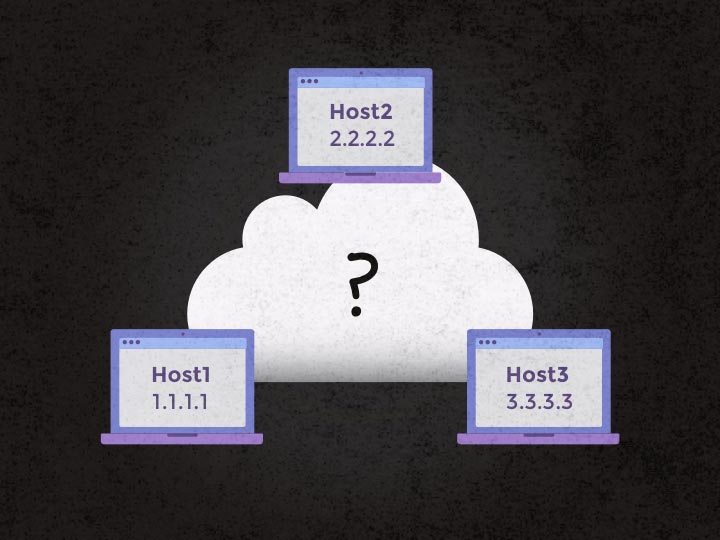






![python的交互模式怎么输出名文汉字[python常见问题]](https://img1.php1.cn/3cd4a/24cea/978/9f39a0b333a15215.gif)

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41100号
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41100号